◎徐思寧、陳潔晧
《蝴蝶朵朵》繪者,長期從事兒童性侵防治、創傷復原的研究與宣導。一同成立「貓獅子工作室」,希望能為創傷復原路上的朋友給予支持與溫暖。
殘酷是另一場殘酷的開端
莎林.科利斯 (Sharyn Collis)十四歲時遭到幫派性侵。媽媽不相信她,說她說謊。她報警,但警察沒有進行起訴。她身心受到很大困擾,不想上課也不想回家。
教育部的心理學家安排李克斯醫生(Dr. Selwyn Leeks)為她進行心理治療。她不覺得李克斯醫生有幫助,只記得醫生不停威脅若她表現不好,便要送她進愛麗絲湖精神病院(Lake Alice Psychiatric Hospital)。(註一)
每個早上的避孕藥
治療進行一個多月後,有一天科利斯回家時看到警車停在家門口,警察強行帶她到愛麗絲湖精神病院。她非常害怕,不想去,但還是被強行帶走。
入院後科利斯被單獨囚禁。她被強迫服用大量精神病藥物。同時,每個早上,她被護士強迫吃下避孕藥,作為「治療」的一部分。
她後來住到六人房,當中包括一名被指控殺害小孩的成人。醫護人員不停恐嚇她若不配合,便把她與殺人犯共同關在籠子內。
電擊與藥物
住院期間,醫護人員對她進行「電痙攣治療」(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正常醫療下,患者會在麻醉狀況下進行電療。然而在愛麗絲湖醫院,很多時候科利斯在意識清醒下接受電療。她的頭會痛得像快要爆炸一樣。電擊的同時,她會失禁、嘔吐並嚴重發抖。
科利斯更被強迫觀看其他院生接受電療。他們有男有女,醫生除了電擊他們頭部,還會電擊性器官、胸部、四肢及軀幹。皮膚會留下燒焦的痕跡。然後,科利斯要清潔他們的排泄物和嘔吐物。
住在愛麗絲湖醫院的青年,常被強迫在「電療」或注射「三聚乙醛」(paraldehyde)二選一作為懲罰。李克斯醫生稱之為「厭惡療法」(aversion therapy)。
「三聚乙醛」是帶有腐蝕性的化學藥物,注入皮膚時會先感到寒冷,然後感到像是燃燒的鐵棒在體內,讓人極度痛楚。被注射的部位會乏力不受控制,失去行動力,身體更會散發讓人嘔心的化學味道。醫護人員還會強迫住院的青年喝下「三聚乙醛」,使他們不停嘔吐,難以下嚥。
科利斯入住期間最少被注射三次「三聚乙醛」。有些青年更被注射超過五十次以上。這是很可怕的藥物虐待。
使用藥物後發生的性侵害
科利斯有時會被單獨帶到小房間,護士用皮帶把她綁起來,然後注射藥物讓她入睡。有次她醒來時,看到李克斯醫生站在床尾,她的上衣被拉到胸部上方,牛仔褲被拉到大腿位置。醫生看到她醒來,對她注射藥物讓她再次入睡。當她第二次醒來時,醫生已離開。她的下體及雙腿感到疼痛,而且有粘粘的東西。她感覺自己像喝醉一樣,迷迷糊糊。她知道自己被醫生性侵了。
每次李克斯醫生為她進行這種單獨的「療程」後,她的陰道都會腫脹瘀傷,並有粘性的分泌物流出。科利斯告訴醫護人員李克斯醫生對她做的事情,但醫護人員說這是因為藥物導致幻想。科利斯告訴媽媽,但媽媽不相信她,指責她說謊。
無處不在的虐待
醫院內發生的性侵害,可用平常來形容。因為除了李克斯醫生外,院內的多名男護士也會對院內的男孩和女孩性侵。護士會在晚上把孩子抓走,不時會聽到孩子被強暴的慘叫聲。有時護士會性侵電療後昏迷的孩子。有些院生接受電療後被單獨囚禁,好幾天被脫光衣服,下藥至昏沉,醒來時肛門極度疼痛、流血和黏稠。
投訴的孩子,會被安排接受更多電療或注射「三聚乙醛」,直到他們不再投訴、不再尖叫。
住院期間,科利斯非常恐懼與不安,因為虐待無處不在。例如同房的一名女孩被護士帶走幾天後,變得神志不清,可能是因為電療也可能是因為被注射了大量藥物。即使醫院有教育局附設的學校,科利斯住院期間沒有得到什麼教育機會。學校的老師也不是可信任和求救的對象。有院生被教師性侵,老師更會威脅如果說出去便讓他接受電療。
虐待後遺症
經過漫長日子後,她終於可以出院了。
她的人生,她的生活,因為入住愛麗絲湖醫院而面目全非。她沒有再去學校。她很害怕外出,害怕人多的地方。即使離開醫院後,她每天晚上依然會反覆夢到在醫院被虐待的情境。
出院後半年,她依然對含有嗎啡成分的處方藥物出現上癮症狀。後來她開始喝酒及出現其他上癮行為。
她感到很難相信任何人,特別是在接觸醫療人員時,感到特別恐懼。她出院後更一直受到嚴重的偏頭痛折磨,需要依賴藥物來舒緩痛楚,但服用藥物又讓她感到非常不安。這些交疊的困難,讓她往後的治療斷斷續續,也讓她難以尋求幫助。
愛麗絲湖醫院的經歷,嚴重影響了科利斯的記憶能力。她記不起十三歲前的事情,出院後即使處理簡單的事也感吃力。她的短期記憶受到影響,使她每天都要努力嘗試記住今天發生的事。更讓人難過的是,她養育了六名孩子,但她不太能記得自己孩子的成長過程。
獨自面對傷害
愛麗絲湖醫院不只摧毀了科利斯的人生,也奪走了她與家人的幸福。有一段時間她感到非常憂鬱難過,人生只剩下黑暗。她無法好好照顧孩子,只能把孩子交給其他人照顧,讓自己可以尋求醫療協助。當藥物療程來到第十八個月,她把所有藥物全部吞下。救護車前來,她告訴所有人,這只是一場錯誤。她清楚知道自己企圖自殺,後來阻止她再次自殺的唯一原因,是她想到如果死了,那麼贏的便是性侵和虐待她的李克斯醫生。
在2002年,傷害她的李克斯醫生依然沒有被究責。她感到憤怒難平。她決定去警局報案,指控李克斯醫生性侵。這是另一次可怕的經歷。她感到警察並沒有在聽她說話。2004年,律師要求警局提供科利斯的報案紀錄,警局卻沒有留下任何紀錄。而在愛麗絲湖醫院的治療紀錄,則充滿了捏造與虛假的資訊。
科利斯2021年出席紐西蘭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全國機構虐待調查」時,已經62歲了。一直以來她獨自面對殘酷的折磨,並且沒有人願意聆聽她的求助,沒有人願意相信她的話語,也沒有人願意保護她。
以醫療為名進行虐待
在1972至1980年間,超過四百五十名兒童及青年被無故送進愛麗絲湖精神醫院。李克斯醫生及院內的醫護人員,對兒童及青年性侵、過度用藥、精神虐待。不論是以過去還是現在的標準來看,大部分在醫院內發生的「醫療行為」,都是一種虐待。
倖存者受到電擊、不當用藥及虐待的影響,他們出院後開始依賴藥物和酒精,以麻痺身心的痛苦並壓抑創傷性的回憶。有些青年出院後選擇自殺來結束痛苦。有些倖存者長期承受身體上的各種不適症狀,包括來自電擊的頭痛、背痛,以及來自性虐待的永久性腸道損傷。很多倖存者的專注力、學習和記憶能力受到嚴重損害。虐待的經歷讓他們無法正常學習和工作,也讓他們往後的人生不停被恐懼、焦慮、羞恥、悲傷和憤怒等難以承載的感受折磨。
第一位提出索償的倖存者
萊奧妮.麥金羅(Leonie Mcinroe)是第一位要求政府賠償的愛麗絲湖醫院倖存者。1994年她在高等法院提出民事索償。兩名精神科醫師證明她沒有入院的理由,以及證明她遭受不當醫療行為。
她本來期待政府可以給予她公平正義,期待政府在得知她在國家照顧期間受到嚴重虐待後,會主動向她道歉和進行和解。然而,政府的代表律師,並不是這樣想。
政府的立場
當政府律師收到倖存者對國家索求賠償的訴訟時,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可行的法律辯護,避免政府的法律責任及減少賠償。
政府當然可以選擇庭外和解,或透過其他替代方案對倖存者進行彌補。然而政府也擔心若開啟了庭外和解的先例,往後需要面對無止盡的庭外和解要求,或需面對大量誇大或是虛假指控。
若國家需要賠償,也意味需要由納稅人的稅金支付,所以政府律師認為有必要採取積極的法律辯護手段,捍衛政府的權益,目的是在保護公共財產以及倖存者索償之間取得平衡。
政府的辯護策略
繼麥金羅的索償申請後,慢慢有更多愛麗絲湖精神醫院的倖存者,以及在其他在精神病院、醫院、安置機構及學校中受到性侵及其他虐待的倖存者提出索償。
在法院審訊中,紐西蘭政府的律師向倖存者採取了多種訴訟策略,以捍衛法律保障政府的權利,例如拖延戰術。
長時間的拖延與等待,對倖存者構成極大壓力與精神折磨。麥金羅案件的訴訟歷時九年,訴訟期間政府多次無故的延遲提供法律文件、不回覆律師信、不停錯過法庭要求的限期。
對政府而言,他們有無盡的資源進行法律抗辯,但倖存者依賴的法律援助則需要每年重新申請審核。漫長的法律訴訟,不但消磨倖存者的資源與意志,更加劇了倖存者及他們家人的創傷。
不惜一切務求避免賠償
除了拖延時間外,政府律師在審訊期間更使用帶有攻擊性的策略。例如要求倖存者到精神病院進行精神鑑定證明自己沒有精神病、在交叉詰問中質疑倖存者為什麼不在受害當下立即揭露、假設倖存者在說謊和串供。倖存者在這歷程不但沒有得到同理及尊重,審訊過程更讓他們感到自己被看待為罪犯或是騙錢之徒。
不少倖存者的索償訴訟中,即使在庭上已證實虐待的發生,索償的要求合理,但政府律師對倖存者表現強烈的對抗心態,堅決在法律框架下尋求迴避責任的策略,極力提出抗辯,不惜一切援引各種辯護的理據,務求阻止倖存者的索償,例如(註二):
.民事索償的法律行使權已過
.依據〈精神健康法〉,所有因善意而採取的醫療行為,有法律豁免權
.要求倖存者提出受虐的書面證明
.要求倖存者證明在國家照護期間受到的虐待,導致後來生活困難
.拒絕披露有關加害者的文件
.調查及跟蹤倖存者,試圖找到對他們不利的個人資訊
結果紐西蘭政府取得不少勝利,成功最小化國家的責任,更有效阻嚇其他倖存者繼續提出民事索償。由於虐待案件的高度敏感和創傷性質,許多倖存者並不希望經歷漫長與嚴苛的法院審訊,自動放棄索償;或是倖存者為了趕快結束審訊,即使感到委屈也選擇接受很低的賠償金額。
被忽視的國家的補償責任
一名童年時在安置機構遭受性侵的受害者,向政府爭取民事索償後,深刻的感受到:「訴訟對政府律師是一種有趣的新遊戲,但對倖存者而言,這是關乎我們的人生。」
在訴訟抗辯的過程中,政府忽視了這些倖存者是在國家照護下遭受了性侵及虐待。這些虐待經歷,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政府沒有在意事實,以敵對的態度,對民事索償的訴訟進行過度的辯護。雖然政府有權利依法為自己辯護,但明顯這種訴訟模式,反映出政府的目光狹隘,缺乏人道考量。這不單對受害者極不尊重,更帶來二次傷害。
兒童及青年在學校或醫療機構遭受性侵及虐待,不是因為他們個人的不幸,而是整個社會制度,一次又一次的辜負了他們,刻意忽視他們的存在。
根據國際人權法,國家對於人民基本權利被侵犯後,有責任進行彌補與補償。政府有道德責任去彌補那些曾在政府機構的照顧或教育下遭遇虐待的受害者。
政府也應同時考量性侵受害者在法院審訊期間需要面對的挫折、時間、壓力、以及他們身心的脆弱狀態,思考除了法院審訊外,有否有其他能回應受害者的替代補償方案。這些補償方案可以是庭外和解、個別機構的補償方案、或是全國性的補償方案。
消失的正義
愛麗絲湖醫院的倖存者,不但經歷虐待及性侵,倖存者更因曾入住「精神病院」,一生飽受社會的歧視與不信任。他們多年來向多個政府部門及醫學團體作出申訴、提告,希望政府及警方展開調查,讓施行虐待與性侵的人得到究責。不過,倖存者不被信任,他們的指控從來沒有得到重視。倖存者一路經歷的,不只是忽視,更可謂殘酷。
2020年6月,聯合國防止虐待小組(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指出紐西蘭政府對愛麗絲湖醫院的虐待事件缺乏進行全面調查並拒絕給予倖存者適當的補償,違反了《禁止酷刑公約》(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然而,直至2022年12月,沒有任何一個人因愛麗絲湖醫院而被究責。而李克斯醫生更在2022年1月過世,生前沒有接受過任何刑事控訴或專業調查。(註三)
愛麗絲湖醫院的倖存者們,至今仍在等待正義的來臨。
註一: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Abuse in care. (19 March 2021). Witness statement of Sharyn Collis, WITN0344007-0001.
註二: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Abuse in care. (2021). From Redress to Puretumu Torowhānui. Vol. 2.
註三: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Historical Abuse in State Care and in the Care of Faith-based Institutions. (2022). Beautiful Children: Inquiry into the Lake Alice Child and Adolescent Un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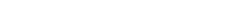

:修補現有兒童安全缺口.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