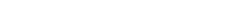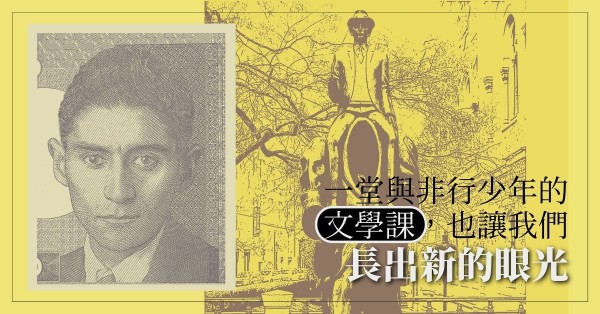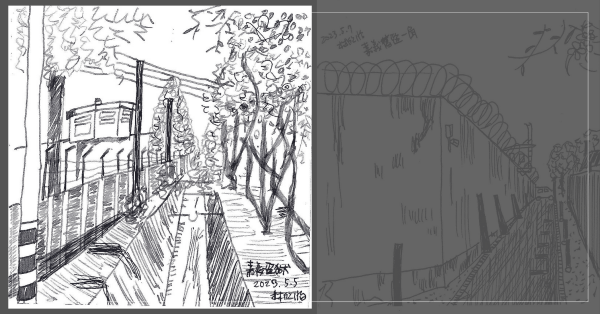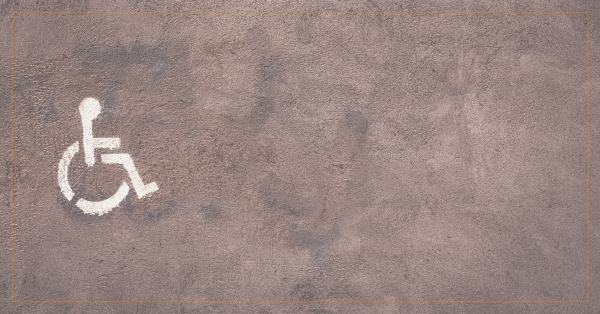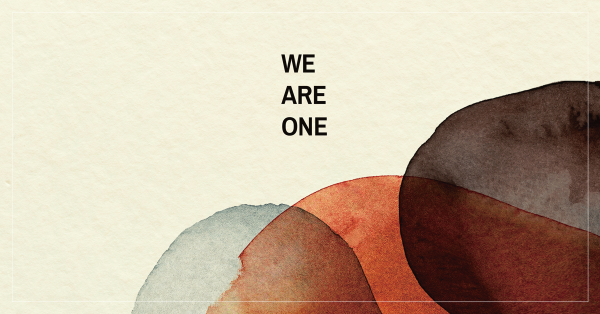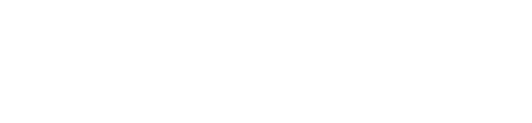◎楊佳羚(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副教授)
「當我想找到愛的人,我通常會先判斷他是不是gay,再想:他願意跟一個障礙者在一起嗎?但我不敢也不願意去找到這個答案。如果我們可以在一起,身為障礙者的我需要被照顧,那麼對方可能就會厭倦我。這個念頭出現後,就讓自己不敢再進一步。我不是自卑的人,但在愛情這方面,也許我真的是個自卑的人。但說不定最後會發現,我找不找得到另一半,跟我是障礙者無關,跟我是同志也無關。」
身心障礙者的性與愛
這段話是2022年12月手天使年度研討會時沅峻的分享。身為男同志與障礙者,沅峻面臨了雙重的阻礙:一是社會大眾認為,女性在社會期待養成下較容易成為貼心的照顧者,因而覺得女性似乎比男性更願意接受障礙者,這讓沅峻不確定能否幸運地找到「願意成為照顧者」的男性戀人;二是台灣雖有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卻仍視照顧為個別家庭的責任,讓障礙者常自覺是家裡的「負擔」,不敢再多要求或奢望自己能有性與親密關係的幸福可能。
而家幗雖在27歲時遇到非常珍惜他的對象,但女朋友的視障爸爸不接受他,還對女兒說:「至少我四肢健全。」無論家幗如何證明自己能開車、能工作及貢獻社會,仍然無法與女朋友繼續在一起。
手天使是提倡「障礙者的性權即人權、手護障礙者性福」的民間社團。從2013年成立至今,他們服務46人次的障礙者,其中只有美女一位女性申請者。從美女的分享文(註一)可以看到,身為女性,更難以面對自己的身體與性。因為美貌迷思,讓開過刀的美女更難覺得自己是「好看」的。這就像手天使年度研討會當天趴趴分享的,因為脊椎側彎,她都不敢展現身體。其實不只是身障女性,社會的美貌迷思,讓大部分的女性都覺得自己難以符合「標準」,永遠都不夠美(註二)。
此外,女性從小就被耳提面命要守貞、要說「不」,讓女性擔心是否自己有了性探索,就不再「純潔」或讓父母失望;再加上障礙者常被視為性的受害者,障礙女性更被要求要好好「保護自己」。這也讓美女感嘆,為什麼自己到了45歲才第一次面對男性真實的身體,為什麼自己比其它女性朋友晚了25年才初次知道什麼是被擁抱、親吻、愛撫的經驗。
文章一開頭沅峻描述的「在愛情面前自卑」的心情,許多人也曾感同身受,卻是我們性教育很少觸及的議題。我們社會總擔心「越教越鼓勵」,殊不知性與親密關係並非一得到性知識就可以立刻展開的。我們的性教育需要更貼近學生的經驗,才能讓學生得以說出自己在追尋性與愛的過程中的不安與擔心。
在手天使年度研討會當天,心路社工透過訪談的方式,讓琮壹分享交女朋友的經驗。琮壹提到爸媽會擔心他被騙財騙色騙感情,別人不喜歡拿障礙手冊的人,但他想告訴大家,心智障礙者可以跟喜歡的人交往,但在交往過程會像上班一樣,需要同事與領班支持,也需要老師幫忙。他喜歡心路有願意幫助他談戀愛的老師。當他被問及「好朋友跟女朋友有什麼不一樣」時,他說:「好朋友是好朋友,女朋友是女朋友;沒有女朋友會讓他覺得孤單、寂寞,覺得冷」。這樣的對話令人動容,也讓人了解:只要老師用適合不同障別障礙者的方式,在教育過程中支持障礙者都可以探索自己的身體、性與愛,讓障礙者有機會說出自己對性與愛的想望;即便受傷,也能得到適合的支持。
讓障礙者成為社會的健檢師
性與愛是馬斯洛所提人的基本需求,但從上述的經驗分享中,會發現我們社會很少正視這些障礙者的基本需求。有人會說,在台灣,連「無障礙空間」都不及格,讓障礙者出了台北市就寸步難行;許多身心障礙者無法自立生活、沒有基本工作保障與經濟安全,面對如此「百廢待舉」的社會,為何要談身心障礙者的性?
這樣的質疑正反映了我們社會缺乏「障礙者的性權即基本人權」的認知,才會將性權擺到後面。性別與障礙研究者陳伯偉提到,在談對身心障礙者的積極「性」支持時,往往發現,身心障礙者就是我們社會的健檢師,幫助我們發現社會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例如,當手天使在訪談時,常發現障礙者諸多內心的擔心與焦慮,與社會的恐性、性道德、男女刻板印象、美貌迷思或健全主義中心有關──這讓我們反思要有怎樣的性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來協助個人探索性與愛的過程。在手天使提供服務前,會發現障礙者往往被過度保護,或在家中難以有獨立的空間──這讓我們思考親子關係與家中空間配置。在安排旅館時,手天使義工們發現難以找到無障礙的旅館或是無障礙只做「半套」──這讓我們更全面檢視道路、交通工具、各式店家的無障礙是否落實。
當我們開始談障礙者的性權,也才能讓社會大眾認知到自己還存在多少對障礙者的歧視:例如,把障礙者「無性化」、「幼稚化」及「受害化」,甚至為了「保護」智能障礙女性,不經她同意就將她的子宮摘除;或是把障礙者「過度性化」,如對於帕運用掉多少保險套的獵奇報導,或嘲諷乙武洋匡「五體不滿足卻『下體大滿足』」。當我們看到障礙者身邊有伴侶時,常認為該伴侶真是「心地善良」;或認為「他都『這樣』了,還想什麼性的事」──這些,都是表面上使用「身心障礙者」取代「殘廢」的歧視字眼,但實際上仍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對障礙者的(微)歧視。
國家對身障者的積極「性」支持
趴趴在手天使年度研討會提到,由於換棉條會比換衛生棉少許多清潔時間,她希望能使用棉條。但國家明令禁止居服員從事這類「侵入性的行為」,即便只是讓女性障礙者生活更方便的協助,也因為這樣的規定而讓居服員怯步。趴趴的經驗,呈現了國家的法規規範限制了居服員,影響障礙者的被照顧方式,而難以有更好生活品質。
反觀丹麥,他們認為對身心障礙者的積極「性」支持,就是給障礙者的日常支持,並且強調「不做就錯」,制定對障礙者的性的國家指引(Guidelines about sexuality: regardless of handicap),積極思考如何由國家提供資源協助、環境打造並培養親密識能。當國家有明確指引時,才能讓協助障礙者的第一線工作人員,知道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不行;也才能讓第一線工作人員知道如何支持障礙情慾。
而瑞典對於障礙者性權的觀點,比較類似台灣對障礙者或對青少年性權的想法,認為「不做不錯、不要喚醒障礙者或青少年的性、障礙者和青少年是性的潛在受害者」。(註三)
瑞典與丹麥同為北歐著名福利模範生,之所以與丹麥有極大的差距,乃因瑞典社會認為性工作就是剝削女性;但在丹麥,給予身心障礙者的積極「性」支持,包含性支持師(sexual adviser)協助障礙者與性工作者細緻溝通,以協助障礙者能得到符合其需求的性服務。台灣的合法性工作只能在「性專區」,但現今沒有任何地方政府有此設置,這也是台灣必須思考的問題。
要落實支持障礙者的性權,除了民間團體的努力,更需要國家資源的積極投入,並思考如何修改相關法令,讓障礙者不再被國家體制霸凌,而能真的得到提升其生活品質的支持,包括「性」支持。
(感謝手天使年度研討會的分享者同意作者記錄其故事,並提供指正。)
註一:手天使官網有許多令人動容的經驗分享文章。
註二: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曾舉辦《礙美。愛美》活動,讓障礙者體驗「變美」的經驗。
註三:對於丹麥與瑞典障礙者的性之跨國研究,及丹麥如何支持障礙者情慾,詳見:陳伯偉,〈讓性empower 障礙者:性不只是權利,更應是社會福利〉,《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9 期p.111-11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