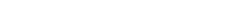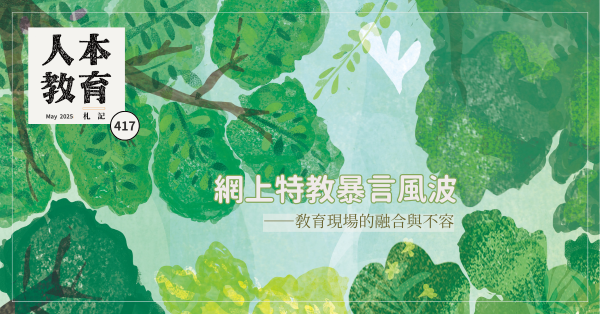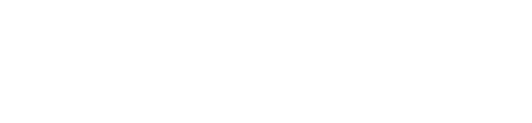◎李昀修
前些日子裡,突然聽人說起有位學生公開了自己受到性騷擾的經驗。
曾照顧這位學生的同事聽聞此事後非常氣憤,趕快跟學生連繫,然而後來,同事分享了一個奇怪的發現。
──學生公開了自己遭受性騷擾的經驗後,朋友們居然都不跟他聯絡了。
加害者並非有什麼交情的對象,甚至是陌生人。但為什麼大家不跟受騷擾的學生聯絡呢?
同事一問才知道,大家是不知能跟受害者說什麼。
「我能問他發生什麼事嗎?」、「想安慰他可是會不會讓他想起不好的回憶?」、「不知道會不會踩到雷?」
同事聽了趕忙說,學生很歡迎有人去陪他聊聊。才緩和了大家的顧慮。
面對性侵、性騷擾的受害者時,往往會加倍顧慮,深怕激起不良反應、讓人感覺被檢討或陷入低潮……而這下可糟了,安慰受害者原本還算是安全牌。現在因為太擔心受害者再度受傷,居然連「這不是你的錯」都不知該不該說,深怕一個不小心就踩到「檢討受害者」的紅線……
陪伴受害者確實不容易,畢竟我們未必具備心理專業;但當我們都把受害者當成炸彈或易碎品來對待時,固然是一種尊重的方式,卻也可能是一種逃避「理解被害者」的鄉愿。
心理師郝柏瑋便告訴我們,在心理治療的過程裡,讓受害者能夠重新連貫自己的故事,才有可能讓受害者的身心都得到放鬆與安全感:「因為人搞不清楚為什麼他不會放鬆的。當事人會經歷到身體的、精神的、語言的連番攻擊,還有『我自己為何不能保護我自己?』的自我批判都要解開,創傷才能慢慢復原。」
曾在人本南部辦公室任職的黃俐雅長年陪伴校園性平事件的受害者,她也談到:「會怕檢討受害者,其實是有善意的,但這份善意再往下想,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質疑受害者,而是為了理解人背後的思考與價值觀。」
而我忍不住問她,過程中會不會反而傷害到被害者呢?
俐雅笑說──所以要沙盤推演啊!然後,要面對自己的「不會」。
「因為我們是人不是神,都會受限於自己的經驗,所以誠實去表達跟接納自己的不會是很重要的。對方才會覺得這不是他的問題。」
嘴上說著不會,可是俐雅的不會,不是要人留在原地,而是謙卑的前行。她提起當年陪伴特教學校性侵案的個案時,自己掉的眼淚比被害者還多,吐槽說自己表現出的是「專業書籍上的不專業」,然而,她相信人能夠感受到情感流動,感受到對方是不是真誠的。
「因為我們也在被他評估啊,累積信任感是重要的。真的想問可以說『如果我問讓你感到不舒服不想講,都可以告訴我,我問問題,不是對你的人格不信任,只是要幫助我自己更釐清。』」
看似一招「真誠」走天下,但俐雅其實先設想好了受害者的擔憂,也替他說出口,盡力的減低了受害者的負擔。這樣,受害者才能把全副心力放在整理自己。俐雅深知檢視的艱難,卻也知道走過這段旅程,能夠讓被害者長出力量,於是她也帶著被害者寫信,有時寫給自己,有時則是寫給加害人。
寫信給加害人聽起來很奇怪,但俐雅說:「寫一封信,可以面質他『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你知道這事情對我的影響嗎?』、『我希望你怎樣怎樣』,也許這封信寄不出去,但之後還是可以把信燒掉,類似儀式化的過程。但不是隨便就寫,因為不知道會引發被害者什麼反應,可能會不舒服會憤怒會需要找人談,那就陪伴。寫不下去,也沒關係啊。」
就像風暴襲來後,人仍然得活下去,面對新的明天。許多人都害怕受害者被激起情緒,然而郝柏偉卻提供了我們一個新的眼光,他提到有受害者會說「你現在坐在這邊講看起來關心我的話,你的工作就是那麼爽」,但作為心理師,他反而覺得開心,因為被害者開始攻擊了,而不是凍結或討好:「攻擊代表他/她恢復感覺,治療中可以持續對治療師表達攻擊或憤怒是蠻好的,這代表他/她稍稍感覺到一些掌控感或權力感,認為──我可以攻擊、即便我攻擊,也可以是安全的。」
而兒少精神科醫師陳質采也提起一位遭受性暴力後終日以淚洗面的個案,對於自己的表現不能像從前一樣好而感到哀傷。陳質采告訴他,你今天受傷了,需要帶著傷一起跑:「但很棒是你想要跑,所以我們可以陪你跑到終點,我覺得是了不起的過程。但不會像你受傷前,你用沒受傷前的自己來評比自己,這樣也很不公平。」
這說法看起來有點嚴厲,但同時,他其實也是語帶疼惜地肯定被害者「想要完美」的渴望:「當這些孩子覺得我再也無法完美時,對自己是不甚公平的說法,等他受傷好一點,他還是可以跑那麼快,我不覺得這是問題。我們希望也許受傷了,但還是可以完成想要的旅程。」
創傷或許帶來的不只創傷,當我們真正想要同理且幫助彼此時,在那之中,也有「療癒」在慢慢滋長。
三位長期陪伴性暴力的工作者,分享了自己以理解、真誠、肯定等方式轉化創傷,都是希望讓倖存者重新做回有力量的自己。
然而,談的雖然是對個人的陪伴,不知為何卻令我想起了前陣子發生在公領域的小插曲。
作家盧郁佳的貼文裡分析了MeToo貼文裡一位被害者母親,提出「人牆論」的觀點,卻讓被害者出面表示這篇文章令母親受傷,盧郁佳也撤文並致歉。我曾想,被害者出面固然有道理,然而盧郁佳的人牆論卻也是重要的討論。這件事以撤文的方式落幕,是否阻礙了對MeToo更深入討論的機會呢?
但在訪談過後,我發現這想法錯了──被害者出面訴說傷痛沒有錯、盧郁佳寫文後撤文也沒有錯,重要的是作為旁觀者的我們能不能夠「接棒」?能不能看懂兩方互動中存在的真誠,能不能明白自己「並不真的明白被害者」卻依然願意嘗試理解與陪伴。
創傷必須要被細緻的處理,但這不能僅僅仰賴少數的專業人士,而是作為旁觀者的社會大眾必須共同出力,一同明白自己「不會」,卻依然願意謙卑地前行。
或許還是會有人受傷,還是會需要撤文,然後真誠的道歉……
但這過程裡,療癒也會發生,然後,社會會前進,雖迂迴且毅然地,朝向更豐沛且同理的未來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