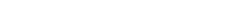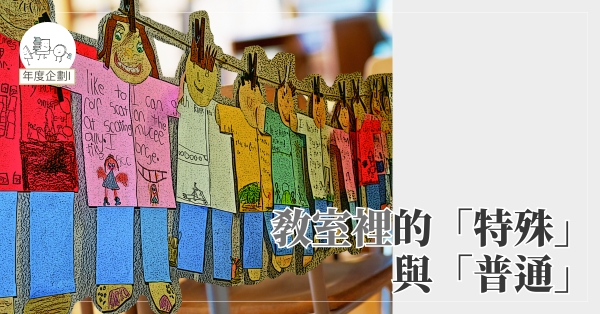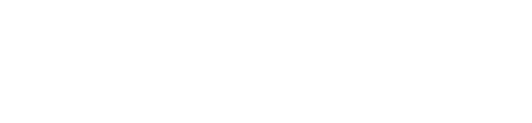◎陳稚宜
五月十日一早我跟著人本同事一行人出發參與「落實家內零體罰,政府該做甚麼事?」國際座談記者會。這場盛會不只有台灣多位立委:張廖萬堅委員、范雲委員、王婉諭委員,出席,線上還有日本、韓國的學者喜多明人教授、野村武司教授、安𤨒鏡助理教授。台灣學者有林沛君助理教授、王美玲副教授。這樣的陣容,讓我又緊張又興奮,落實家內零體罰的第一哩路,就要展開了!
「一邊打,一邊講道理」的家庭教養困境
開場由人本教育基金會馮喬蘭執行長報告〈家長育兒教養需求問卷〉網路調查結果。近8成家長贊成立法禁止家內體罰,其中有53.6%的家長是在有配套措施的條件下贊成。這其實呼應了這場座談的大方向,家長需要的是協助,而不是抗拒立法禁止體罰。這是政府在思考立法時要優先考量的事情,事實上,也是從現在開始就可以努力的事。
另外,馮執行長提到有96.5%的家長曾經以講道理及溝通的方式管教孩子,顯見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孩子的權益,以及他們其實不想打小孩。雖然如此,仍舊有近四成家長(39.2%)會以體罰作為管教手段,66.3%會責罵小孩,而有56.3%會處罰小孩。這種矛盾正呈現出家長們處在育兒實況與理想上的拉扯。一邊打一邊講道理的困境,需要被解放。(更完整的問卷調查報告請見本期札記〈「我其實也想正向教養」問卷裡的家長心聲,與來自立委與學者的意見〉)
張廖萬堅委員聽完馮執行長報告後也隨即回應,家內體罰的修法至今尚無突破,包括民法1085條: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的問題。也就是家內體罰在民法是可以的,但什麼樣的懲戒才是合理的?這是值得討論的,並且我們也需要父母親職教育資源的投入,才能發揮更實際的幫助。
但實際運作可以怎麼進行,就要更進一步從三位日韓學者提出的日韓經驗借鏡起。
借鏡日韓立法經驗
我非常好奇日本、韓國為何能在這兩年完成立法禁止家內體罰(日本2020、韓國2021)。他們跟台灣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也都有相類似「愛之深,責之切」的教養觀。我猜立法過程受到的阻礙,應該不小,那他們是如何看待跟面對?又有哪些作法來支持立法呢?
專門研究教育學和教育法學的早稻田大學教授喜多明人說,日本於2019年6月頒布了「防止虐待兒童法」,並且修訂「兒童福利法」,明文禁止父母和法定監護人以教養名義進行體罰,同時日本也成為了全面禁止體罰的國家之一。但即使頒布了禁止體罰的法律,父母的意識也沒有改變,根據日本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 Japan) 2018至2019 年的調查顯示,有超過6成家長承認「有過不得不做的體罰」。由此可知,還有為數不少的家長認為體罰是不可避免的教養方式。除了零體罰意識尚未明朗,體罰的問題也不只是身體上的處罰,還有來自父母的精神暴力,尤其是來自信奉升學主義父母的壓力與譴責,與傷害小孩人格的言語暴力,這些都被稱之為「教育虐待」。
喜多教授在這裡停頓了一下接著說,而且孩子們不會求救!這是目前日本的一大課題。為什麼孩子們不說?喜多教授說:「因為對孩子們而言,不說反而可以獲得某種安全感,而且他們早已意識到若發出求救訊號,反而會導致危險。」
因此,保障兒童的權益、建立一個讓心靈受創的孩子可以安心諮詢,並可以發出 SOS 求救的救援組織是日本目前的一大課題。自 1998 年兵庫縣川西市將兒童人權監察員制度化以來,目前日本 43 個都道府縣的地方自治體根據該條例也成立了公共第三方維權組織。日本律師協會在各地設置了收容逃離施暴父母的庇護所,以保護孩子們有逃離家長的空間與喘息機會。除了有庇護所的措施外,日本也正在朝著廢除民法父母和法定監護人的懲戒權邁進。
針對喜多教授提到民法懲戒權的修法,來自東京經濟大學現代法學部的野村武司教授,也表示這是日本當前最重要的課題。野村教授提到二戰後頒布的《學校教育法》規定,校長和教師可以管教學生,但不得體罰學生,這個禁止校內體罰的規定被延續至今。但在家庭方面,民法規定,父母有權利及義務對孩子進行監護及教育,而且可以對孩子施予懲戒。讓日本從1990後半,虐兒致死案例攀升,野村武司教授說:「針對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雖然我們有《防止虐待兒童法》來保障兒童不受家內體罰,但我認為在民法中的父母懲戒權,仍然需要修改。」
另外,野村教授也與喜多教授提及了相同的現況——日本的零體罰教養還沒跟上。甚至,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審查裡也明確指出「日本雖然立法禁止體罰卻沒有得到實際成效。」我聽著,也想這是因為整體儒家思想要改變還是需要非常多年吧。改革之路總是漫長,接著野村教授話鋒一轉說「無論如何,法律的制定反映了社會公眾對家內零體罰問題的認識,但僅靠法律的約束,是無法改變人民的意識,如果要施行全面零體罰,我認為人民的啟蒙是必須的。」
東洋大學安𤨒鏡助理教授延續了野村教授的話題分享了韓國的現況:2019年韓國廢止了父母懲戒權,但實際上還沒完全地被實現。主要原因是,大眾對孩子的想法還停留在「孩子是不成熟的人格主體」。韓國也受儒教文化、父權主義根深蒂固的影響,大部分父母親都會認為孩子是自己的附屬品,尤其是她們絕對不能反抗長輩。安𤨒鏡助理教授說:「對小孩而言,我們是利用力量、暴力迫使他們服從於我們,這也是需要大眾換位思考與改變的地方。」
另一方面,懲戒權廢除後(2021年4月)民意調查結果說明:知道禁止家內體罰的家長以及孩子的比例非常低(家長33.3%,兒童20%)。因此,韓國政府致力於推廣改善社會大眾意識的文宣,文宣中提到「父母和小孩都要幸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因為很多受到體罰的世代都已經是成年人了,讓更多成年人了解如何避免體罰,並持續性的推廣改變社會大眾的傳統概念。
從三位教授的簡報中,可以體會到,立法,可以視政府決心而努力,而且是必要的一步,然而「重新看待兒童」、「突破傳統教養文化」、「(成人)擺脫自身成長經驗」將是整個立法過程要仔細照顧、面對的文化問題。
落實家內零體罰,親職措施可以怎麼做?
座談會上提出了落實家內零體罰,政府可以努力建構的親職支援系統:
一、提供專業、有效的親職教育:
政策應鼓勵、支持各種處境家庭都能獲得親職教育。並要確認講師能對兒童權利有正確認識,且能提供具體有效方法。
二、增加親子友善空間:
友善兒童的空間並不該被視為一個「將親子隔離於社會之外的場域」,所以還應透過更多宣導及措施安排,讓人們普遍更友善對待親子。
三、建立良好的托育系統:
要建立托育系統的公信力,無論是人力品質、硬體品質,督導系統,都應完善,使家長能放心。
四、提供育兒喘息服務:
目前喘息服務多在長照系統,但親職也有此喘息需求。政府宜提供或協助媒合具一定品質的臨時托育服務。
衛生福利部保護司司長張秀鴛在現場回應時提及兒少權法正在修法,將會往這些方向考量,但的確民法父母懲戒權是個阻礙「當社工在判斷兒少在家內是否受到不當對待時,都會因為民法父母懲戒權而影響判斷。因此,回應到相關配套上,懲戒權需要修法外,更重要是民眾對於所謂一切形式的暴力概念的理解,特別是在家內管教行為的界線,要跟家長有更多溝通。」
從司長的談話,我可以感受到善意,但目前政府的決心似乎不夠明確。法入家內,確實需要謹慎看待。一般人們會將親子管教視為「私」事,然而維護兒童能有充分發展並享有兒童人權公約所列之各項保障卻是政府的責任。各國之所以(不只日韓)立法禁止家內體罰並研擬各項政策配套,是因為不能將兒童所遭遇的一切,都只歸咎、歸責給父母,政府也必須提供相當資源,扛起應負之責。
我可以了解,今天能有這場座談會,代表著台灣社會進步的累積。是因為過去幾十年各界的倡議及努力,有越來越多人在思考要擺脫舊包袱,也有越來越多人關注要讓台灣能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但也就是因為看到這個基礎,對於下一步如何邁進,如何盡快落實,我們有更急更深的關切。這場座談會提出很多反思以及確切可行的做法,就是要促使政府能邁開步伐,展開家內零體罰的第一哩路。期待,結合民間與政府的力量,我們可以建立台灣成為一個「讓兒童安心長大無需帶著創傷」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