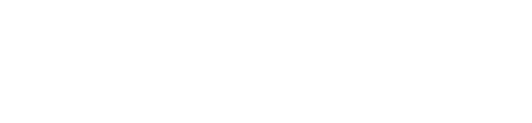◎史英
森小,大家耳熟能詳了,就是人本在汐碇路那所;但這次要講的事情,卻是發生在苗栗一所國中。大家會想,怎麼會這樣呢?那是因為,那所國中裡有一個「森小分班」,而森小分班裡的景色,當然也算是「森小風景」了。
你會想,蛤,現在國中裡可以設小學分班了嗎?我們的教育體制,當然還沒有開放到這個地步,而且,那個森小分班,也確實是一個七年級的國中班──只是因為導師教數學和帶班,走的是森小風,所以,我們就大膽稱之為森小分班了。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有一個「破解地獄梗教案」(註1),雖然森小高年級,和另一個小三的分班,都上過而且很精采,但總是比較大的孩子較能討論。因篇幅所限,我們還是只「播放」國中的風景就好了。
那天早上,老師先在班上放了「抖音」中的一段「地獄梗」,內容是嘲笑侏儒症的(註2)。據說,2/3的小孩都看過那個頻道(!),而這次一班廿幾個中,只有一個小孩看完沒有笑。
接著,老師帶大家確實理解那個「梗」的意思(很多小孩沒真的看懂),之後,問第一個問題:為什麼笑?哪裡好笑?各種回答整理起來,大概是:接到梗覺得很好笑;反差很好笑,雖然很可憐,但反差時笑了;因為主持人或同學笑所以笑;一開始覺得很好笑,看著看著覺得很可憐,再看一次理解後笑不出來……
課堂的氛圍是,小孩逐步意識到自己的笑,其實「有多種層次」;剛好下課了,老師覺得停的剛剛好。
隔了一天,上地獄梗的第二課。一開始,先誇獎大家討論的很「細膩」,再把上次「為什麼笑」歸納為幾個層次,讓小孩「想起自己的前天」。然後,就提出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叫做地獄梗?
這次小孩的回應可以分成三類:要想一下所以叫地獄(後來被大家反駁);因為違反倫理,笑的人要下地獄(佔全班2/3);因為會有個被笑的對象,那個對象會下地獄(這個佔1/3)。看起來,就是有約1/3的小孩還不太進入狀況。
接著,老師帶大家從影片裡釐清,也請大家重新想想從小聽到的下地獄的情境;最後,全班都同意,是看了這梗會笑的人要下地獄──但有人補充:對被笑的人來說,現在就是地獄!
接下來,老師問第三個問題:製作地獄梗的目的是什麼?明知道會害別人下地獄,為什麼還製作?
問題越來越深了,而小孩的回應也與時俱進:為了賺流量;貶低別人覺得自己很厲害;別人不敢(製作歧視梗)我敢;讓別人覺得我不怕下地獄;一面說下地獄一面笑,就是讓看的人覺得大家都這樣,也就不怕;就好像平常我們做錯事總拖人下水……
老師做了總結:製作地獄梗,可以覺得自己很厲害,只靠幾個梗,就打敗大家的同情心,這時,全班驟然安靜了一下。
老師問第四個問題:當我們把這些歧視當成戲謔時,有想到新聞的哪些事件?小孩毫不猶豫地說出:台大經濟系系學會競選文宣,光復中學模彷納粹,中一中用「烯環鈉」暗指原住民(不知道老師什麼時候帶他們討論過這些)……
下午起床(午休後),老師先發一人一支冰,再說他們討論的多麼好,還說,連遠處的史老師都鼓掌鼓掌了;然後,就進入地獄梗的第三堂課。
老師提第五個問題:討論這麼久,我是希望你們不要再看嗎?(全班說不是)你之後還會再看嗎?(幾乎都說會,除了四人)那你覺得以後再看,還會不會笑?
幾乎所有小孩都說會(老師說:我有抽一下),但有人補充:只要我知道我在笑什麼,而且還有確保我的同情心還在就好!老師再問那四個,為什麼不再看地獄梗了?回答是:我沒把握我的同情心會不會默默不見了!可能不小心就不見了!!我覺得要一直確定不容易啊!(老師說:我雞皮疙瘩掉滿地)
最後,老師播放「從眾」的影片(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以及重播「台大經濟系學會競選政見」(小孩驚呼:這個是地獄梗嗎?),但老師並沒有再多說什麼。
最後,全班的感想大概趨於一致,就是,同情心,同理心,是要好好維護的。
隔天,老師轉述了我跟她說的話:雖然我很希望他們開始「痛恨」那些會笑以及製作地獄梗的人,但我知道──不能用歧視(痛恨)歧視者來反歧視啊!據說,小孩聽到「不能用歧視(痛恨)歧視者來反歧視」,笑得非常開心。
老師也跟我說了這樣的話:怎麼上地獄梗的課,感覺好像在上數學?但我無法轉述給全班,只好轉述給各位親愛的讀者了。
註1: 《破解地獄梗教案》見https://living.hef.org.tw/notes/detail/2/485
註2: 參見註1教案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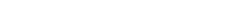








[1].png)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