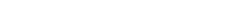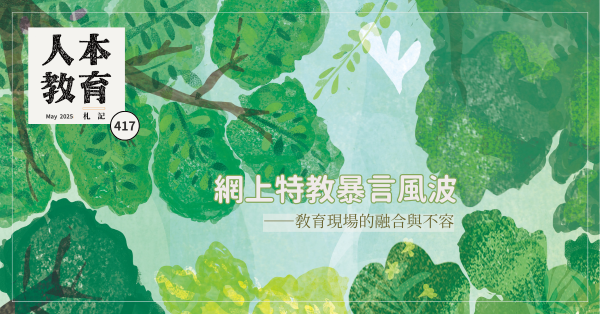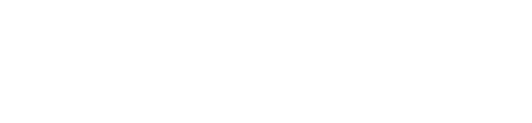◎廖佩汝
MeToo運動給了許多受害者說出「自己版本」故事的勇氣,卻也引來留言區的質疑,不少人問受害者「為何當下不呼救、不逃跑?」很快地,有網友舉出美國資深心理治療師彼得.沃克在《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裡提及的4F生存策略(註),說明在性侵害如此重大的創傷發生時,「僵住(freeze)」是再合理不過的,沒能呼救或逃跑也無可厚非。
這解釋令人沮喪,雖然說明了為何大多性侵受害者無法反抗,可同時也像在說,我們從神經生理機制上就被編碼成無法使力的反應,只能任由悲劇發生。
如果不願接受這個結局,透過各式網友的MeToo文章,我們發現早在性侵發生前,被害人就已經歷某程度思維的「僵」,比如儘管反感又疑惑,卻還是進了房間、上了車、脫了衣服。既然「僵」似乎是個漸進過程,我們猜想,是否有辦法在最後關頭前,透過覺察這樣的反應機制來思考突破的可能性、從而解除僵硬狀態?
為更全面理解問題,我們訪問到心理諮商師郝柏瑋,以及兒童精神科醫師陳質采,邀請他們以自身專業角度與大家探討此議題。
被推翻的猜想
郝柏瑋心理師聽完我們的猜想後,馬上說明在「僵」這個籠統說法下,其實還必須區分出層次。僵反應如同光譜,是人面對危險時出現的求生模式:思想,比如上課分神;情緒,說起自身故事像在說別人的;身體感受,像是失去痛覺或麻木無感;記憶,常見的為創傷失憶;人格,也就是解離,把痛苦經驗切割,分給創造出來的新人格。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層次不是漸進的發展順序,強烈受個人歷史經驗影響,每個人有不同的觸發源(trigger),無法一概而論;且創傷發生當下,多混雜有語言、肢體、精神、自我評價等面向的衝擊,混亂複雜的情境使得過程幾乎無法預測與掌控。
談到這裡,我們已經發現先前的猜想過於簡化。本來我們認為,「僵」應當有個程度不斷上升的可預期過程,所以只要想辦法在抵達頂峰、完全僵住前,瓦解這反應,就能讓被害者即時脫逃。
事實上,基於個體與情境差異,面臨創傷場面時,有人想都不想就會立刻抽離情緒,也有人就直接解離了;且此過程經常像推骨牌,一旦有感知被切斷,其他也會陸續斷開,若沒有當下立即介入協助,完全攔截不了。
你的反應不是你想像中的反應
「但難道整個事發過程,真的抓不到一點思考介入的間隙嗎?」我們不死心,繼續追問。
我們舉例,受害者提到自己「腦袋一片空白」的同時,也會提到「現在發生什麼事?他在幹嘛?我要跑嗎?」粗淺推論,真正的「一片空白」應該像驚嚇,是完全沒想任何事,但很多故事聽起來並不是這樣。這是個好消息,代表受害者當時仍有一絲思考餘力,有機會自主脫離「僵」的狀態,對嗎?
針對我們的論述,首先陳質采醫師認為,個案撰寫受暴經驗比較像是以冷靜的狀態在寫「回憶錄」,回想時自然會加入各種後設描寫,並不能真正反映她當下的思考狀況。
接著,醫師沉默一陣後道:「人在危急時的反應並不像平日理性的思考或決定,那不是一種理性判斷,而是先被恐懼制約或淹沒。」大腦有個構造叫杏仁核,對情緒反應十分重要,尤其會儲存高度攸關生死的「恐懼」情緒,以便往後看見相關危險時立刻觸發,傳導神經訊號,使心跳加速、手心流汗、肌肉緊繃。
換句話說,那一瞬間我們並不是「思考後感覺害怕」,身體的反應遠比思緒跑得更前面,即「一看見就害怕」了;對所見所聞的瞬間恐懼是你的反應,不是你的判斷。
至於反應的模式為何?「危急時能依據的只有曾經想過的方法。」當陳質采醫師這麼說時,我們想起郝柏瑋心理師也曾感慨道:「人很難做出自己以前沒做過的決定。」
意思就是,一旦杏仁核偵測到危險(所謂的危險可以相當個人化,即郝柏瑋心理師與我們提過的個別的”trigger”),恐懼機制自動引發後,一個人接下來的反應模式並不根據此刻當下,而是過去的習慣——事發當場,你如何戰、逃、僵、討好,實則是被你過往每一次的經驗決定的。
理直氣壯的防災演練之路
兩位不謀而合的觀點看似導向了一個悲觀的結論,卻意外地為我們帶來另一種想法:我們能不能做「防災演練」?
要在危急時刻做出特定的反應,勢必需要練習。地震防災演練的效果使我們不必在天搖地動時判斷「桌子穩嗎?還是躲衣櫥?天花板會塌下來嗎?」而能直接反應要鑽進桌下保護頭部。過往經驗之於深陷恐懼的我們如一條救命繩,是混亂中能安心抓住的浮木。當然,那根浮木可以是「開門跑到街上」,也可以是「躲到桌下」;可以是「徹底切斷感覺,停止痛苦」,也可以是「無論如何,想辦法離開現場」。
然而,這個「防災演練」比地震演練費時,且嚴格來說,得從我們還很小的時候開始。
郝柏瑋心理師表示,華人禮教中較缺乏身體自主權的觀念,更傾向暗示你「你的感覺不重要」。常見的狀況是,眼看孩子已經又哭又躲,父母仍不以為意:「你要大方一點!」、「給叔叔抱一下會怎樣?」、「人家是喜歡你才抱你!」有自主意識以來,我們經常感覺不安全,卻被逼著為他人的需求妥協。
在這種社會互動下長大的孩子,哪還有辦法主張「身體是我的」?在他為了那些陌生長輩的「喜歡」,害怕得斷開感受、任人擺布九十九次後,你怎麼能期待在第一百次,有師長說因為「喜歡」而想脫去他的衣服時,他能做出不同的反應呢?
陳質采醫師則認為,讓孩子認識自己的身體,與主張身體自主權的理直氣壯密切相關——「你最喜歡身體哪裡?你能跑多遠?跳多高?」女生自小被教導要文靜、乾淨、端莊,大多舉止含蓄且不喜歡運動,因而失去很多打開四肢、施展力氣、試探環境的機會;身體缺乏練習,加上文化與教育的功勞,遇上危險時遑論戰鬥,逃跑通常也不在選項中。
肯定身體,確認經驗,釐清喜歡與討厭,並練習確實將感覺反映在日常行動上;反感就遠離,疑惑就找藉口開溜,不輕易接受「只是我想太多」。唯有如此,當面臨恐懼混亂時分,我們才有機會不斷開感覺、不抽離,不接受委屈勉強的選項。
防災演練之路漫漫,我們應當銘記在心,卻也不必戒慎恐懼。
陳醫師隨後感嘆「認識身體」實在不該是為了預防性騷擾而存在時,我們大力點頭贊同。身體是美好的,與身體相處是參與世界的重要體驗之一,甚至,當你全心感受著肌肉的拉扯、發熱的皮膚、動靜態的張力與平衡時,或許不必任何人教導,你也會深刻感受到,身體是你的。
註:4F生存策略為戰(fight)、逃(flight)、僵(freeze)、討好(fawn)。